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知识生产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代。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“体制时代”,即知识生产大多来源于体制内、或与体制粘附性的知识分子人群,包括诗人、学者、官员等。无论多少他们的思想多么前卫,或者左、中、右,他们多少与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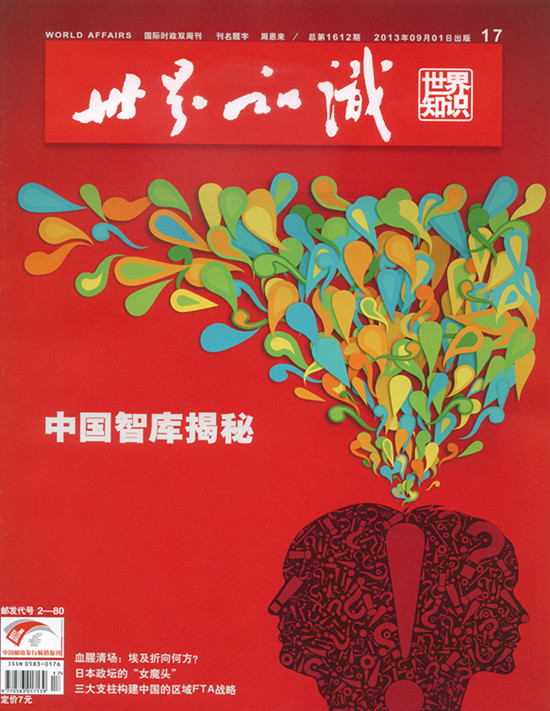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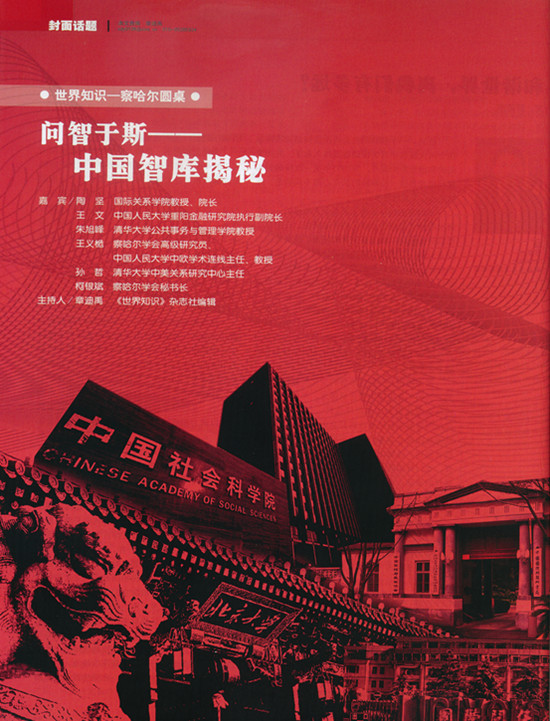
原标题:中国知识生产进入“智库时代”
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王文
该文为最新一期《世界知识杂志》封面文章
时代呼唤“智库时代”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知识生产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代。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“体制时代”,即知识生产大多来源于体制内、或与体制粘附性的知识分子人群,包括诗人、学者、官员等。无论多少他们的思想多么前卫,或者左、中、右,他们多少与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到了90年代中后期,随着媒体市场的开放,以及文化体制的市场化,整个知识生产进入了“媒体时代”。大量新知识(如新概念、新名词、新结论或新描述)实际上是通过媒体打造与传播出来的,一批优秀的媒体人――尽管他们有的是躺在知识出版的背后――实际上是知识生产的真正主力。
但现在,随着微博、微信等自媒体的壮大,信息变得过于碎片与喧嚣,传统媒体与专业媒体人的影响力下降,加之体制内学者受到束缚无法充分发声,社会需要真正严肃的知识生产。这就需要一批专业的知识生产者,即智库学者。这类学者需要了解体制的运作,也需要懂得媒体的运作方式,更需要深谙研究之道、拥有问题意识以及家国情怀。从这个角度讲,时代呼唤着知识生产进入“智库时代”。
智库学者有别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一般学者。一般学者追求的是学术研究,并通过核心期刊的发表,以体现自己的学术能力,与社会、政策的关系度并不是必然的。但智库学者却有着严格的功能定位,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到金融经济研究,从社会研究到政治研究,智库学者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发掘、影响与改善现实问题,具有强烈的今世致用的目标,以及学以致用的情怀。
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办的。2012年9月上海重阳投资向人民大学一次捐赠2亿元,成为当时最大的一笔单笔捐款。2013年1月19日,人大重阳正式成立,明确提出“立足人大,放眼世界;把脉金融,观览全局;钻研学术,关注现实;建言国家,服务大众”的24字方针,把金融报国、知识报国作为智库的宏愿。在过去半年内,出版了数十篇重要报告,公开发表了近200篇评论,对不少议题产生了社会影响力。这可以算是知识生产“智库时代”的一个应证吧。
“智库时代”的三个特征
从主体的变化角度看,“智库时代”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征:
一是高校智库的壮大。近年来,高校智库明显呈增加的趋势,原有的一些研究机构也明确表示转型为智库,纷纷产生影响社会问题、政策议题的意愿与目标。
二是民间智库的增多。有很多民间智库,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社团或公司,以某种知识推广或政策改变为己任,不盈利,但由重要的资本或财团支持。类似的民间智库越来越多。
三是官方智库的转型。比如说中国社科院搞创新工程,还把过去几个大的研究所合并成研究院,明确表示要研究转型。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、安全部下属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近年来的改变也不少。
“智库时代”的中国意义
“智库时代”的到来,对中国来说意义不同凡响。大体看来,至少有以下四点:
一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全新需求。政治现代化必然面临决策的民主化、透明化,必然会出现传统政治中“黑匣子”、个人专断的终结。未来的政治决策不得不寻求智库的智力支持、咨询,甚至建设性的批判意见等等。近些年来,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越来越活跃,越来越多知名学者被请进中南海,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现。
二是中国学术功用化的突出反映。几年前,美国学者约瑟夫•奈曾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,提出学术研究的两个功用,为了政策(for policy)、为了学术(for academy)。事实上,学术功用化还有一个目标,即为了社会。把学术内容用简明平实的语言,通过各种媒体使官员和老百姓得以理解,这就是学术的功用化,也是影响社会、影响政策的重要途径。约瑟夫•奈本人就是既写学术文章,又写政策报告,还是评论文章写作的高手。
三是中国社会权力化的必然目标。目前,中国社会的崛起趋势明显。老百姓越来越关注国家大事,并通过新媒体反映出个人对政策的诉求。决策者也越来越关注老百姓形成的社会力量,于是这种力量很自然地反映到了一批专门收集、发掘社会关注点、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智库学者笔下,于是有了智库报告,进而去影响决策,或者说代表老百姓参与决策进程。
四是中国智库产业化的最终结果。正如美国智库业的现状,中国智库的未来一定是产业化的,即有明确的生产者、有知识产品、有销售与营销人员、有渠道、有消费者等分工与定位。半年多,人大重阳的实际运作就是不断往那个方面去做尝试,许多议题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。
对中国智库未来的七点建议
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。在我看来,这些支持可囊括成七个方面:
一是制度改革。现行的官方研究机构的体制不利于知识产品生产。有时现行的学术体制会培养出懒惰的研究人员。学术评价体系只拘于职称、核心刊物等,不太利于学术功用化的拓展。另外,智库学者与官方之间的旋转门制度也应尽早确立,可以通过挂职等方式,请一些智库学者到官方机构任职。
二是资金投入。资金投入不能只靠政府要钱,而要通过其他社会途径的支持。只有来自社会,才能服务于社会,才更有助于智库研究的独立性。因此,智库学者恐怕得转换思想,改向政府要求为向企业、向社会要研究经费。
三是人才培养。首先是写作和编辑人才。一般学者特别偏好学术化的语言。某位金融高官曾对我说,“写金融内参真的需要一个好编辑,否则太多专业名词,真的难以卒读。另外,智库学者除了有研究能力之外,本身应该有丰富的中文功底,以及整体把握问题的能力等等。
四是良性竞争。美国研究圈虽然也有互相批判,但整体上的诋毁、文人相轻现象比中国要少得好。中国智库业要发展得很,中国学者之间多一些鼓励,少一些互踩,恐怕是有必要的。
五是渠道拓展。智库的内参材料需要有高效的输送渠道。产品送不到需要的人群手里,就不可能有好的影响力。此外,智库学者还要充分利用电视、网络等媒体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。
六是问题意识。该研究什么、不研究什么,智库学者必须要很高效的取舍。能发掘问题,并能提出解决至少改善问题的办法,是智库学者必须要有本领。
七是中国本位。现在不少学者在研究问题时站的立场很成问题。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学术现象。但无论如何,站在中国、站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,应是智库学者的本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