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时间:2017-02-28 作者: 王文
中国智库确实正在蓬勃发展,但发展速度仍然跟不上国家的发展速度。中美智库的差距就像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差距,不在于单个演员的实力,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不足,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落后。中国不应全盘复制美国的智库模式。
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、教授,本文刊于2月28日一条财经微信公众号。
智库的英文名为think tank,用王文的话说,智库的深层意义正如其英文名“思想也有像坦克那样的威力”。不过,中国智库是否也具备这等实力呢?对此,智库联盟专访了这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(以下简称人大重阳)执行院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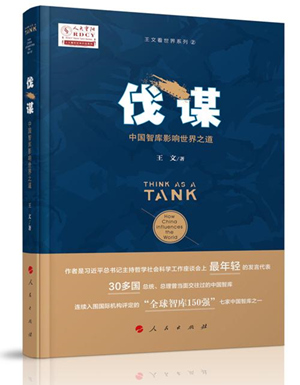
诚如王文在其新著《伐谋: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》中所说,中国智库确实正在蓬勃发展,但发展速度仍然跟不上国家的发展速度。中美智库的差距就像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差距,不在于单个演员的实力,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不足,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落后。但王文也反复强调,中国不应全盘复制美国的智库模式。
中国智库接下来该如何发展,特别是官方智库的机制体制创新力依旧不足,智库学者的待遇较低、激励不足等问题该如何解决,王文给出了他的答案。
以下根据专访实录整理:
中美智库的差距在于对智库思想的整体营销力
智库联盟:我们发现,现在只要有智库排名,人大重阳就在其列。从2016年清华大学公布的中国智库谷歌英文搜索量,人大重阳排在第一位,到今年连续三年入选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《全球智库报告》“全球顶级智库150强”,是否可以说明人大重阳的国际影响力?
王文:其实,所谓智库排名,只能反映智库发展的一个侧面。我一直认为,中国的好智库有不少,人大重阳只是晚辈后生,有时甚至根本配不上那些排名,还需要兢兢业业、扎扎实实的工作很多年。
但另一方面,相比较其他入围榜单的中国智库,人大重阳的人员数量并不多,属于精干型。如何以相对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,人大重阳做出了有益的探索。
智库联盟:您认为现阶段,中国智库在世界的影响力如何?与国外智库相比,还存在哪些不足?
王文:中国是智库大国,但不是智库强国,中国的智库数量是排在世界第二位,但有国际影响力的还不多。中国学者在海外发文章的其实寥寥无几,但海外学者发的文章,很多我们这边都有翻译,中国学者发的文章能有多少篇被美国翻译?美国有名的学者一般来中国都会有相对高昂的出场费,中国学者被邀请的也有,但很少有出场费的。再比如,美国的知名智库学者基辛格,每次来中国领导人都接见,但中国学者去美国很少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。
我走访过美国智库街数十次,“智库街”位于华盛顿西北部、距离白宫仅三四公里的麻省大道,那里坐落着几乎所有能够孕育美国经济、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大智库,随便走进街道的某家咖啡店、餐馆都能遇到某位著名智库的学者,我偶遇过的人物包括美国时任财长保尔森,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等。那些常年在那边工作的智库人员,相互间接触是多么高频率,高质量的思想火花也很容易在频繁接触中产生,而中国智库人员的交流多限于正式研讨会,远没有美国那么频繁和轻松。
总结起来,大体有如下几点:
一是产业规模。美国智库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,智库(think tank)这个词组就起源于“坦克”,即思想也有像坦克那样的威力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,美国智库已达近2000家,均是年均预算达到数百亿美元、从业人员超过十万的产业规模,中国现代智库开始在中国发展则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。
二是运营机制。包括筹款、人员管理、项目运营等的完善和思想市场体制的形成。相比之下,中国智库行业还处在初级阶段,远远落后于国家发展,不少中国智库的功能性定位还不够清楚,官方智库“千库一面”,更多听从自上而下的安排,运营几乎全部都靠财政拨款,独立性较低,效率较低,难以赢得社会与企业的深度认可,也很难获得大额的社会捐款。而中国民间智库的思想生产,则很难找到真正的消费者,加之内部运营能力参差不齐,融资运营机制尚未成熟,更不可能大范围地得到社会捐赠。不少咨询公司自称“智库”,借智库大发展,浑水摸鱼,使得所谓民间智库界变得鱼龙混杂,脱颖而出的优秀民间智库并不多。
三是机构影响。两国真正的差距在于对智库思想的整体营销力,包括项目设计、调研、撰写、评估、报送、传播、社会文化、政治结构等各个环节。中美智库差距很像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差距,不在于单个演员的实力,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不足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落后。
中国智库在美国智库面前毋须妄自菲薄
智库联盟:但为什么前段时间关于美国大选的预测,美国智库几乎全部预测错了。
王文:这是另外一个评判标准,智库的评判标准有大小之分,还有对错之分。就大小来说,美国智库的影响力数十倍大于中国智库,但就对错之分,中国智库就不必妄自菲薄了。
当然,客观原因也有很多,一是美国这么多年的霸权,二是美国智库还是有英语通用的优势,中国大部分的优秀智库学者英文水平都不行的,这个对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也是有很大影响的。另外,我们的学者大部分都很腼腆,愿意多写内参,不愿意去宣传炒作,美国却是一个市场竞争,善于运用媒体给自己贴金,成为了一个生产链,去炮制一个学者的形象,就像炮制明星一样。
其实几次见到基辛格,我曾问他,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战略家,那么多智库学者,给决策层提供建议,但是依然没有抑制美国不断在战略上犯错的现实,也没有抑制这些年来美国不断衰落的趋势。中国的智库学者可能很内敛,但实际上我们默默为国家做过了很多贡献,相对踏实、务实,为我们的政策把关、决策咨询、科学民主化、决策科学化、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做出了实在的贡献,这种贡献其实并没有被社会全部看到,尤其现在中国领导人重视智库之后,很多媒体都开始采访智库,过去是很少的,智库学者到底做了什么,大家并不完全知道。但其实不管是影视作品中还是回忆录中我们不难看到,从改革开放到现在,各种各样的政策,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制,到90年代初期的市场经济改革,还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出台,背后都凝结着我们各类智库的智慧,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,这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了智库的作用。
智库联盟:人大重阳跟国外智库主要的合作模式是怎样的?有没有案例可以分享?
王文:人大重阳跟全世界差不多五十个国家有合作关系,合作紧密的是一些大国,比如美国、英国之类的,各大洲都有。
去年有个案例,被评为“2016年十大对外传播案例”中的第一大案例。人大重阳与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2016年的7月5号,办了一个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,这个时机特别好,在7月12号南海仲裁案公布前的一个星期,在美国华盛顿,离白宫不到两公里的地方,我们邀请了两国最著名的学者和不少前官员,还有很多媒体,事先的发出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声音。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先生做了重要主旨发言,其中一句话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报道,“南海仲裁案不过是一张废纸”,这种智库间的合作就是搭建这样一个平台,示范双方政府的声音,互通、交流,互相试探底线,进而管理危机。
设立“一带一路学”并不超前
智库联盟:人大重阳将很多重点放在“一带一路”上,您也提出要系统研究“一带一路”,甚至提出应建立“一带一路学”,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?
王文:“一带一路学”的提出,很多业内人士是很重视的,因为这体现了中国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。“一带一路”实际上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人自己提出的概念,引起全世界如此大的关注、研究、考量的这样一个理念,当然应该做更系统的研究。很多人觉得太超前了,但是我认为学科就是因为现实的发展以后出现的。红楼梦越来越流行有了红学,敦煌一百多年前被发现,后来有了敦煌学、国际关系学。1919年,在伦敦第一次设立国际政治的学科,还不到一百年,新事物的出现当然应出现新的学问。
当然,“一带一路”覆盖到全球,肯定不会一帆风顺,会有困难和风险,但是风险的大小会与议论的多少成正比,风险越大,议论越多。“一带一路”能有如此大的影响,是超乎我们最早的意料的,人大重阳算是较早研究“一带一路”的智库,我也走了不少地方,看着“一带一路”开花结果,这已经非常难得了,但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和验证中国参与、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后期的效果。
智库联盟:新形势下,中国智库还应做哪些创新工作?
王文:中国领导人在2013年5月第一次提到建设新型智库,已经过去几年时间了,中国智库确实也有了一些蓬勃发展,但我觉得智库的发展速度仍然跟不上国家的发展速度。最关键还是智库,特别是官方智库的机制体制创新力依旧不足,智库学者的待遇也较低,激励不足。我认为,还是应重新推动智库的市场化改革,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改善智库供给的质量,因为智库是思想的供给者和生产者。现在中央是非常支持智库的,智库本身也应该更努力。(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:@人大重阳,微信公众号:rdcy2013)